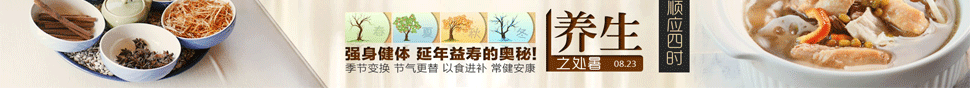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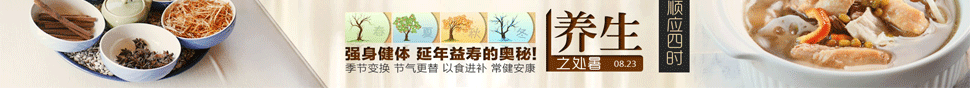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苏文忠公海外集
琼州海口海南书局民国卄三年版
一、苏轼海南时期诗歌的思想内容苏轼在海南所创作的诗歌今存首①,这是其海南时期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部分。这些诗歌内容丰富,是苏轼晚年贬居儋州时期思想感情最为美妙的艺术表现。记录生活,是苏轼在海南期间的诗歌创作中最丰富的部分。苏东坡是一位热爱生活,又擅长于把日常生活转化为诗歌的人物,本来很普通的生活,在他的眼中往往富有浓厚的诗情和哲理,从而用美丽的诗歌表现出来。如元符二年()年冬至日,一群邻里乡亲各自携带着酒菜器具,由符林、吴老率领着来到桄榔庵找苏东坡聚餐饮酒,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却触动了苏东坡父子的诗情,苏轼《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写道:小酒生黎法,干糟瓦盎中。芳辛知有毒,滴沥取无穷。冻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饛。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里闬峨山北,田园震泽东。归期那敢说,安讯不曾通。鹤鬓惊全白,犀围尚半红。愁颜解符老,寿耳斗吴翁。得谷鹅初饱,亡猫鼠益丰。黄姜收土芋,苍耳斫霜丛。儿瘦缘储药,奴肥为种菘。频频非窃食,数数尚乘风。河伯方夸若,灵娲自舞冯。归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传张长公。和诗仍醉墨,戏海乱群鸿。[3]诗中描写、叙事、议论浑然一体,场面生动,作者的感情溢于言表。苏东坡在此诗题下自注云:“符、吴皆坐客,其余,皆即事实录也。”[3]一个“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4]2的诗意栖居者,对生活只要实录就够了,正如林语堂谈论苏东坡时所说:“如果作家的思绪很美,只要他能忠实、诚恳、妥当表达,美丽和美感自然存在。”[4]2表达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旷达超脱精神,是苏轼海南时期生活诗篇中最具特色最有意味的部分。当时儋州是一个“黎、蜑杂居,无复人理,资养所给,求辄无有”[5]的地方,海峡对岸的海康已经是最为蛮荒的地方了,而儋州“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5],在中原人士看来简直是非人所居之地。苏轼面临这种物质匮乏、文化落后的生活环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艰苦困顿的生活表现在诗歌之中。但是由于苏东坡生性狂放、自由、幽默,加上兼备儒家的安贫乐道、佛家的平常态度、道家的超然物外的精神,又使他在诗中常常同时表现出超脱旷达来。如他在儋州贫病交加,苏辙又劝他不要读书,于是作诗曰:“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使君不复怜乌攫,属国方将掘鼠余。”[3]他使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汉朝太守黄霸见到官吏们工作辛苦,在路旁吃饭,乌鸦飞来把肉叼走了,黄霸怜悯他们,回到府衙后慰劳他们。苏东坡用这个典故说,现在我倒好,在儋州根本就见不到肉,这免得太守为之生怜悯之心了。另一个典故是汉朝苏武出使匈奴不辱使节,冰天雪地中生活,饿得挖老鼠洞找老鼠吃剩的东西,东坡借这个故事说自己差不多与苏武一样了。本来身心是那么痛苦空虚,但是他却用这样的语调使痛苦的情绪在幽默中淡化了。再如他听说住在雷州的弟弟苏辙身体消瘦了,这本来是很伤心的事,但是苏东坡却写诗说:“从来此腹愧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并告诉苏辙说身体消瘦并不是坏事,“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3],如此一来,悲伤的情调没有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在此轻松幽默的诗句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他还记录了生活中许多有趣有味的事,如《观棋》记载了自己不善下棋而观看儿子与军使张中下棋时的感受,表达了对棋文化杰出的见解。《谪居三适》等作品则表现出苏东坡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能够寻找到安适的生活方式的本领。身为谪臣,却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黎民百姓,关心着海南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反映于诗歌,成为苏轼海南诗歌中非常富有价值的主题。当时海南农业极为落后,与全国以农业为本、重农轻商的大背景十分不协调,再加上汉人统治的剥削,成为制约海南经济发展、使黎民百姓陷入艰苦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苏东坡无权改变这种局面,只能拿起诗笔,创作了《和陶劝农六首》,诗序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3]在这组诗中,苏东坡首先提出了“咨尔汉黎,均是一民”的民族平等思想,并对汉人鄙视、欺骗、掠夺黎人而不能加以正确的教化引导的政治现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指出了黎人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农业意识薄弱、游手怠惰、不习礼仪等。他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耝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3]最后他为黎人百姓描绘出一个美好富足的生活图景: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3]他提倡重农的努力使儋州风气渐渐好转,元符二年()他看到了热闹的鞭春图景,遂创作了一首《减字木兰花》词作: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遍丏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6]作者一口气用了七个“春”字,浓郁的鞭春风情和作者喜悦的心情洋溢其中。当地文化、教育观念同样落后。苏东坡目睹冼夫人庙“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的荒凉景象,感受到风气之衰,甚是痛心,于是产生“我欲作铭志”“我当一访之”,恢复冼夫人祭祀,兴起礼乐以教化人民的决心。(《和陶拟古九首》之五)[3]他看到城东学舍空空如也,“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只有一个先生“忍饥坐谈道”,如此荒凉,正是此地教化不到、邦风毁坏的缩影,遂发出“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的感叹,流露出要像古代贬谪南荒的虞仲翔学习,推行教育,使弦歌遍于沧海的心愿。(《和陶示周掾祖谢》)[3]经过努力,情景发生了好转,终于能听到儿童的读书声了,遂以诗记之曰: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且欣习齐咻,未敢笑越吟。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荆榛短墙缺,灯火破屋深。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3]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当时的喜悦之心溢于言表。苏东坡在海南有一些赠友之作,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友谊的珍贵。宋人费衮有云:“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7]苏东坡在海南情况又更为复杂,他与远方亲友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少得多,也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每有“人事断绝”[5]“亲友疏绝”[5]之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人的关怀显得特别重要,苏东坡往往以诗报之,另外对一些优秀的学生也曾赠诗。这些诗感情真挚,如《赠郑清叟秀才》《赠李兕彦威秀才》《葛延之赠龟冠》《别海南黎民表》等,而最具感染力的是三首赠送军使张中的五言古诗。苏东坡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元祐党人领袖,政敌对他的迫害是可想而知的,在他遭受打击的时候,几乎所有与他关系密切的生友也相连而遭受打击。在此情况下,很多人都远远躲开了他。张中作为苏东坡贬谪地的最高长官,不仅没有遵照政敌的意愿迫害东坡,反而尽一切可能关怀、帮助东坡父子,与东坡父子结下深厚友谊,并因此受到冲替的惩罚。对这位就要离任的军使,穷困至极的苏东坡无以回报,只能以一首诗送给他: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暂聚水上萍,忽散风中云。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3]首句谓可能从此要永远分别了,为全诗打下了基调。接下来赞扬张中是能够与黎民相亲爱的好官,回忆张中对自己的关怀。“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在强装旷达中流露出将要永远分别的痛苦。最后二句表现出无以报答张中深情厚义的惭愧之情。张中由于留恋东坡先生,虽然罢任,但“屡不成行”(王文诰题下按语)[3],一再推迟行期,于是苏东坡又有了二送、三送张中之作。依依惜别之情状流溢于字里行间,真挚感人。纪昀叹曰“此首真至”(诗下王文诰引)[3],王文诰曰“其张中恋恋不忍去之状,情见乎词矣”(王文诰题下按语)[3]。苏轼是一位善于适应环境的诗人,他对陌生环境的认识和融入总比别人快,也总能把一地的风物在他的诗歌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海南岛地理位置独特,具有着与中原大陆迥异的热带风光,以及在此环境中形成并相对独立发展的风情文化,这些内容在苏东坡绝大部分海南诗中或多或少的有所描写,有些诗歌表现得比较集中,有些诗专为咏物而作。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3]据此诗的长题可知,作者是在上巳日携酒遍寻诸生,而诸生皆已出门,独老符秀才在家,相饮大醉,因知海南不作寒食,而在上巳日上坟的风俗。诗中虽然一半篇幅用典故表达自己的现状,而首句和末句则是记载了海南上巳日上坟的风俗和这个时节独特的景色。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其二)[3]-把与大自然高度融合的黎家村寨和口吹葱叶的农村习俗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五色雀》则是专为海南人眼目中的吉祥鸟所作:粲粲五色羽,炎方凤之徒。青黄缟玄服,翼卫两绂朱。仁心知闵农,常告雨霁符。我穷惟四壁,破屋无瞻乌。惠然此粲者,来集竹与梧。锵鸣如玉佩,意欲相嬉娱。寂寞两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陈雪肤。举杯得一笑,见此红鸾雏。高情如飞仙,未易握粟呼。胡为去复来,眷眷岂属吾。回翔天壤间,何必怀此都。[3]诗前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焉,俗谓之凤凰云。久旱而见辄雨,潦则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尝一至庭下,今日又见之进士黎子云及其弟威家。既去,吾举酒祝曰:‘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乃为赋诗。”[3]苏东坡从当地人听闻此鸟之奇异,验之果然,因此写下了这首咏物诗。苏轼笔下的黎幽子是第一个走进中国纯文学创作的完整的黎族人形象: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之九)[3]虽然在东坡笔下多有黎家百姓和读书人出现,但是要么是顺便带过,要么是汉化程度高的黎人。专门以一位介乎生黎与熟黎之间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这是唯一。我们从这首诗中至少读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诗中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完整的黎族人形象,这是一次对被正人君子所鄙视的黎族人的正面描写,我们看不到任何歧视的口吻,而是更多地感受到人格的尊重,这在古代文学史中是第一次,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二是苏东坡与海南百姓尤其是黎族人民的良好关系,从中可见一斑。当人们沉浸在苏东坡对于海南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深远贡献之时,也注意到了苏东坡居儋三年海南人民对于苏东坡生活的关怀与支持。这首诗大概就是海南人民尤其是黎族人民敬爱苏东坡并予以关心支持的最早记录了。东坡《观棋诗帖》局部
二、苏轼海南期间和陶诗的心理历程苏轼晚年在海南时对自己的和陶之举十分满意,曾写信告诉苏辙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5]东坡和陶之举起于北宋元祐七年()扬州任上,而其和陶能够真正进入渊明之境界,是到了晚年贬谪惠州和海南时期。与惠州时期相比,海南时期又有鲜明突出之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数量上看,东坡和陶作品总计为首,其中在海南所作,据王文诰《苏轼诗集》所编顺序,计有56首之多,几近全部和陶的一半;二是苏东坡对陶渊明诗美的经典评述及对淡远型诗歌美学的终极追求是在海南时期完成的。如此看来,海南时期的和陶,数量上与惠州差不多而略胜;陶诗美学的探讨上则比惠州时期更加深刻。苏东坡在海南和陶的过程,正是他到海南之后自我调整心态的过程,是心灵净化的过程,是在困苦中求解脱的过程。无论他最初发起和陶之举的动因何在,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海南期间的和陶,是与他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及其孤寂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写信告诉苏辙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喜好渊明诗歌之美固然是其和陶的原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他在同一封信中接着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5]渊明有“此病”而能早知,又能够达到随性所适、于世无所困的境界。苏东坡亦有“此病”而不能早知,能知时而又身不由己,连进退都不能自主,更何谈对一切世事的随性所适。既无渊明之境,则在遭受挫折时也就难以泰然处之,不能泰然处之,则难免心中悲戚,苦痛忧懑随之而生。此东坡所以深愧渊明而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原因。苏东坡曾多次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3]“我其后身盖无疑”[3]之类的话,但这只是苏东坡感觉上与陶渊明性情上的相通,而并非说达到了渊明的境界。所以他刚到海南而沉入痛苦绝望的感情低谷的时候,读陶、和陶便成为他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以晚节师范渊明之万一,再则是为了消化眼前的困苦之境况。他说“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5],又说“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唯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5],和陶也是“随意所寓”[3],皆为求得心灵的慰藉。我们从头细读苏东坡至海南之后的和陶之作,就能看到一个清晰的线索,苏东坡的心态在暗暗发生着变化,心情在慢慢好转。绍圣四年()四月,苏东坡于惠州接到再贬海南的诰命,心境一度落到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不幸,对家人交代好后事之后,与家人泣别江边,独携幼子苏过踏上贬谪的征程。本年六月十一日到达海南,七月二日到达贬所昌化军,很快就开始了和陶。至本年年底,和陶诗已达41之多。这半年之间的和陶诗虽然内容复杂,但充满其间的感情基调是相当低沉的。有的诗中充满着孤独自怜之感,表现出精神上的痛苦,如梦归惠州白鹤峰、出郊步月、荷叶杯等。《和陶九日闲居》是由于重九前夜不能寐,起而索酒之所作,也是心中孤寂的表现。《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云:“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3]诗中流露出对于儿子的歉疚和孤独之感。有的诗则感于海南的蛮荒落后,是他初到海南尚未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状况的表现,如《和陶示周掾祖谢》写游城东学舍,见到的是久已荒废的空舍和一位忍饥谈道的先生。《和陶劝农六首》则是哀悯于海南农田荒芜、农业落后而作。《和陶拟古九首》“客去室幽幽,服鸟来坐隅。引吭伸两翅,太息意不舒”[3],不免令人想起贾谊的《鵩鸟赋》之哀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苏东坡在和陶过程中一直努力追求着与陶渊明的趋同。“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有了与渊明的神游,他的心情在发生着好转:“还将岭茅瘴,一洗月阙寒。”(《和陶东方有一士》)[3]-在这样不断的神游净化过程中,苏东坡心头的寂寞、不平和凄苦在不断淡化着。然而直到绍圣五年()春,苏东坡的心头仍蒙受着莫名的阴影。他到达贬所之后,寄居在官屋之中,虽然有军史张中的照顾,但苏东坡的心中总有不安。他曾试图卜居城北废园,但是忧惧之情袭上心头,因为他在惠州时刚刚建好新居就遭到再次贬谪的厄运,现在仍心有余悸。他担心政敌不肯干休,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和陶使都经钱溪》中表达此时的感受:“但恐鵩鸟来,此生还荡析。谁能插篱槿,护此残竹柏。”[3]苏东坡的担忧不久就应验了,政敌派员把他赶出官屋,仓促之间他不得不一度露宿桄榔林下。大约在绍圣五年()初夏之间,苏东坡为陶渊明关于形、影、神的吟咏所感发,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作了一次深沉的哲学思考,用《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三首诗,紧接着陶渊明的话题进行阐发。第一首诗中写到形的悲哀:“梦时我方寂,偃然无所思。胡为有哀乐,辄复随涟洏。”[3]第二首写影的见解,它认为形的局限在于实在性:“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影自己的优越性在于“无心”,不需要担忧什么:“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虽云附阴晴,了不受寒热。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别。”[3]最后是苏东坡把自己更为深刻的思考寄托于神的言论: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平生逐儿戏,处处余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3]神把精神与肉体分开进行论述。有形必有虑,既然把精神与形体分开来看,那么也就没有形体之累,无形体之累,也就可以抛开肉体所面临的一切束缚,求得精神的解脱。如何达到解脱?苏东坡认为佛教和仙道都不可靠,都是虚无飘渺的,非现实的。现实的解脱以陶翁的做法最为亲切,也最为可行。在现实中抛开形体之累而于精神中达到解脱,这是苏东坡所要追求的陶渊明的境界。经过彻底的思辨,苏东坡与陶渊明越来越接近了。苏东坡在儋州,除了和陶诗之外,他还追和《归去来兮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3],大约即在此时所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彻底谢官归乡后之所作,充满了“觉今是而昨非”的愉悦。东坡和此作,说明其心态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调整,初到海南时的那种绝望、悲凄之心已经难以看到。绍圣五年()年四月,苏东坡住进了自己的新家桄榔庵,此后所作的十多首和陶诗,基本上没有了悲哀的色彩,先前沉重暗淡的笔调消失了。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年版
三、苏轼海南时期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苏轼是一位各体兼备、风格多样的诗人,五七言古体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词,无不得心应手。通观苏轼在海南时期的诗作,却是偏重于古体诗的创作。在今存首诗歌中,古体诗达91首之多(除十多首七言、四言之外,都是五言),近体诗为32首,词4首。苏轼在海南期间偏重于古体诗的创作,与他晚年醉心于陶渊明,和陶、学陶的意向与创作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体诗虽然数量偏少,但佳作连连,七言律诗如《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六月二十日渡海》《儋耳》,七言绝句如《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纵笔三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五言绝句《儋耳山》等,词《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都堪称东坡诗歌的佳品。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诗歌创作风格,与其诗学思想大概是一致的,大略可分为平淡高远型、峥嵘绚烂型,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潇散旷远型。陶渊明式的淡远诗风是苏东坡在海南时期诗歌美学及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苏轼对自己的和陶成就十分自负,曾告苏辙说:“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5]可见他认为自己的有些作品达到了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我们读东坡海南和陶之作,大多具有淡中有味的特点,表现出作者向陶渊明的趋同,许少作品可谓形神兼备。但二人在许多方面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故苏东坡在学习陶渊明淡远风格的过程中,自然带有个人的特点,刘熙载《艺概·诗概》谓“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刚,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相掩也”[8],正指出了二人不同之处,各得其美。就淡泊的纯度而言,苏轼恐有不及陶渊明。而在才力、思力、笔力和心胸等方面,苏东坡都远过于陶渊明,因此苏东坡有些和陶诗在思辨深度和气度上超过了陶渊明,如《和陶形增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三首具有哲学思辨的作品,虽然苏东坡的结论是,要获得现实的解脱,必以陶渊明的做法为高明;而就诗歌本身的深度、广度和气度而言,陶诗实为逊于坡诗。和陶诗之外,有些古体诗也同样达到淡远的艺术境界。如《观棋》: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3]此作采用四言体式,多用典故而人不觉,如《诗经》一样古雅,却多出一份空灵。纪晓岚评价说:“纯用本色,毫不依傍古人,而未尝不佳。”(王文诰按语所引)[3]乾隆皇帝推崇备至,认为“清幽静妙,真得味外之味。”[9]苏轼在海南期间,虽然极力追求者淡远诗美理想,但并没有放弃他惯常的那种峥嵘绚烂、豪纵超迈的风姿。他在海南最早创作的两首五言古风可谓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其一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行琼儋间肩舆做睡》)[3]苏东坡自惠州接到再贬海南的诰命之后,心情一度陷于低沉状态,但是在他还没有达到贬所昌化军之前的途中,海南无比奇异的风景却触动了他那雄放豪阔的胸怀,以大视觉和奇丽的思维,创作出如此峥嵘豪放之作。乾隆评此诗曰:“行荒远僻陋之地,作骑龙弄凤之思,一气浩歌,而出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足当司空图‘豪放’二字。”[9]豪放而不粗豪,故纪昀从艺术境界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杳冥诡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为上乘。”(王文诰按语引)[3]苏东坡作此诗后,兴犹未尽,复以同韵创作一首: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下视九万里,浩浩皆积风。回望古合州,属此琉璃钟。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渡海十年归,方镜照两童。还乡亦何有,暂假壶公龙。峨眉向我笑,锦水为君容。天人巧相胜,不独数子工。指点昔游处,蒿莱生故宫。(《次前韵寄子由》)[3]此诗视野更加开阔,气度更加开展,风力更加雄健。王文诰在“下视九万里”句之下注云:“自此以下,高唱入云,有叫阖排阍之响,声彻九天九地矣。”[3]乾隆则评曰:“其胸次实为天空海阔,非是无聊解免之词。”[9]长篇古风如此,近体诗中也有如此风力之作,如绝句《儋耳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3],律诗《儋耳》之“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杆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3],皆如苏辙所云“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0]的作品。有些作品显示出来的美学特征,既不像陶式淡远型那么内敛,又不像峥嵘雄放型那么张扬,往往是语言平淡,真实朴素,而又气象外露;自然清新,潇洒自如,而又韵味悠长,可归为潇散旷远型。七言绝句多数属于这一类型。如《登澄迈通潮阁二首》《纵笔三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先觉四黎之舍三首》《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纵笔三首》云: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3]-乍一看,三首作品都好像在漫不经意间客观地叙述着一种情景,但是仔细读来,正如王文诰在本题之下评价的:“此三首平澹之极,却有无限作用在内,未易以情景论也。”[3]第一首的“一笑”,表面上似乎冲淡了悲戚,而同时也加重了悲剧色彩。绝不让悲戚蔓延传染,却一定要让真实的心境几乎不留痕迹地保留在字里行间。纪晓岚所谓“叹老语如此出之,语妙天下”(王文诰按语引)[3]云云,此之谓也。第二首“溪边古路三叉口”,语言最为平淡,却也最有冲击力,因为这一句转出独立斜阳数过人的图景。作者没有发表任何情感,但我们如果仔细体会细微之处,便会感觉到,一位一生忠国爱民,曾经做过正三品的大学士和许多地方长官,学贯古今的文坛领袖,却仅仅因为戴了一头乌角巾而为海外百姓所争看,无所可用,无人理解,无可诉说,只能独立于斜阳之下,古道之旁,一个一个地数着不相干的行人,这是多么悲哀的图景啊!但是我们在诗中找不到一个悲哀的字眼,却宛如欣赏一幅闲雅古朴的夕阳独立图。难怪王文诰在第三句下评曰:“此三首之第三句,皆于极平淡中陡然而出,而此句尤奇突,殊不知‘争看’二字已安根矣,三首皆弄此手法。”[3]难怪纪晓岚在末句下叹曰:“含情不尽。”(王文诰按语引)[3]第三首写由于北船不到,米粮断绝之时,苏东坡想到明天祭灶带来的情景。大诗人困苦的处境已经让人心里够难受了,但作者突然想到明天邻家的祭品一定可以得到分享,于是禁不住一阵高兴,冲口而出。老人这种如孩子一样的真率,被纪晓岚感赞“真的好”(王文诰按语引)[3]。但任何一个对诗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过来,纪晓岚的赞叹只是在诗歌艺术层面上的,事实上,正是老人这无比真率的盼望,愈加反衬出老人处境的悲哀。没有一个字提到悲哀,但无限悲哀在其中;虽然其中蕴含了无限悲哀,但老人却以轻快的真言出之,正是因为他不愿让悲哀扩散蔓延开去。吴鹭山等人评价说:“纵笔三首,萧散闲适。虽故作谐语,但也写出作者贫病交加的困境。”[11]其实贫病交加并不能概括其中的全部。更加丰富而深刻的悲剧情境与闲散语风的完美结合,才是作品千载以下让人涵泳不尽的潜因。宋代许觊谓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12]指出苏轼海南时期的诗歌艺术可与李白、杜甫、陶渊明、谢灵运相抗衡。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13]所谓宋人之说,乃朱弁的言论:“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14]文学史及朱弁的这两段话对我们理解苏东坡在海南期间诗歌创作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坡仙笠屐图宋濂题字本
四、苏轼在海南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苏轼海南诗歌在北南宋之交的盛行,宋代的朱弁有下面一段记载: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5]从字面讲,“海外诗”指海南苏东坡的诗歌。根据古人的话语习惯,虽然这段话所叙的并不一定局限于苏东坡在海南的创作,但是文中既然突出了“海外”,则其海南之作必定甚为重要。可见,苏东坡海南时期的诗歌在当时以及其去世后不久,就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海南之士以及曾在海南做官的人士,十分重视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创作,收集编辑成《居儋录》和《海外集》,成为海南历史上最早的诗文别集,其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乃是诗歌。此集备受世人推崇,如乾隆四十年儋州郡守萧应植在《海外集序》中说:“夫坡公诗文,地负海涵,雄视百代,学者固当力窥全豹”,而在不能获得全集的情况下,《海外集》已经弥足珍贵,“资其言论文章,以为高山景行,则一鳞一爪,未尝不可会神龙之全体,幸勿以崑山片玉而少之也。”[16]1陈景埙《重修海外集序》说:“昔人谓公放浪岭海,其文益伟,力斡造化,元气淋漓。今读其书,浑涵光芒,自作一家,浔所谓‘一代文章之宗’矣。”[16]1可见在清代人眼中,苏轼早成为海南文学之宗师。就诗歌而言,苏轼也是被推为“辟南荒之诗境”(王国宪)②者。苏轼在海南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与他在整个海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分不开的。苏东坡在海南历史上,实具有文化教育的开创之功。清代陈烺《重修东坡书院有感》:“宋朝一日攻朋党,儋耳千秋得太师。”③陈景埙《重修海外集序》谓苏东坡“一言一行,海表钦式,其为功于琼之人者,正复不小”[16]1。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序》的大部分篇幅在论述苏东坡对海南的开化之功,其开篇云:“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郎朗,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④文末又强调:“文忠公之教泽,流传千古矣。”《儋县志》则明言:“吾儋自宋苏文忠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王、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迄乎有元,荐辟卓著。明清之季,多士崛起……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⑤清代刘凤辉《居儋录序》说:“自公谪居此邦,德教所盛,优游濡染,骎骎有声名,文物风开琼南风气者,非公而谁哉?”[17]《琼台记事录》载戴肇辰的论断:“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⑥则成为评判苏东坡海南历史地位的经典论断。文化教育观念和风气的转变,必然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苏东坡的学生中,琼州人姜唐佐成为第一个海南本土的举人。昌化人符确也是受苏东坡濡染者,继姜唐佐为举人后,又成为第一个海南本土的进士。《儋县志》中所列其他有成就的文士也都是“自宋苏文忠公开化”之后而成材的。宋代的科举虽重策论,但作诗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中消失过,因此他们必须过作诗这一关。从这个意义,完全可以判定这些科举成功之士必为善诗者,只不过他们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而已。他们同时产生辐射作用,影响到整个海南的知识层。他们是第一批海南本土诗人,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师承传递,推动海南诗歌的创作,经过南宋和元代的默化孕育,至明代而迎来海南诗歌创作的辉煌时代。大概从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海南著名学者和文献学家王国宪在《琼台耆旧诗集》的凡例中指出:“琼台风雅开自东坡,盛于有明,……爰逮清朝,人才辈出,风雅复盛。”[18]综上所论,苏东坡在海南诗歌史上实具有开创之功,正如他在整个海南文化教育史上的开化之功。东坡自题金山画像望坡书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注释:①此据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统计。包括贬琼途中于梧州所作的《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及于雷州渡海前夕所作《和陶止酒》,前者有“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之句,后者引云:“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颂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二诗皆与海南关系密切,可作为研究对象。首诗中,个别作品是否作于海南,学术界有争议,但数量极少,对诗歌史的宏观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②《儋县志》(上册),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1页。③《桄榔庵、东坡书院历代诗选》,《儋县文艺增刊》,儋县东坡书院管理处年编,第8页。④《儋县志》(上册),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1页。⑤《儋县志》(下册),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页。标点略有校改。⑥见:[同治]琼台纪事录:不分卷/清#;戴肇辰、云逢晟修纂.——海南师范大学馆藏海南地方文献古籍线装书复印本.——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年.——1册.原版为清同治八年()刻本。参考文献:[1]庄逸云.简论韩国古代诗话对苏轼的接受[J].琼州学院学报,(6):10-14.[2]万燚.论华兹生的苏轼诗译介[J].琼州学院学报,(6):1-9.[3][宋]苏轼.苏轼诗集[M].[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4]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海口:海南出版社,.[5][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6]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7]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G].长沙:岳麓书社,.[8]袁律琥.艺概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9][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0][宋]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1]吴鹭山,夏承涛,萧湄.苏轼诗选注[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2][宋]许觊.彦周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55.[14]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G].中华书局,:.[15][宋]朱弁.曲洧旧闻[M]//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6][宋]苏轼.苏文忠公海外集:卷一[M].海口:琼州海口海南书局,(民23).[17]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附录[M].海口:海南出版社,:.[18]王国宪.琼台耆旧诗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3.TheComprehensiveStudyonSuShi’sPoeticCreationinHainanLIJing-xin(SchoolofHumanities,HainanTropicalOceanUniversity,SanyaHainan,China)Abstract:PoeticcreationisthemostcrucialpartofSuShi’sliteraryachievementsinhisthree-yearstayinHainan.TherichpoetictopicsarethewonderfulartisticpresentationofSuShi’sthoughtsinhisexilelifewhile“HeTaoPoetry”reflectshismentaladjustment.Hispoemsarealmostinpre-Tangstyleandtheartisticstylesareroughlydividedintoplainandlofty,toweringandsplendid,andnaturalandunrestrainedpatterns.AstheliterarymasterinHainan,SuShi’sstatusandinfluenceinhistoryofHainanliteraturerelyonhishighpositionandfar-reachinginfluenceinthewholeprocedureofhistoricalandculturaldevelopmentinHainan.Keywords:SuShi;Hainan;poetry——相关连接点开了解——
1.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6|东坡六题
2.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5︱苏东坡?黎母山?东坡石
3.海南贬谪文化研究系列(8)︱李景新︱苏东坡居儋时期的养生理论与实践
4.李景新|海南贬谪文化研究系列(5)|论苏东坡的海南功业
5.欧阳修苏轼居颍诗词中的酒文化
6.东坡生日诗词寿苏
7.一树梨花压海棠:看苏东坡怎样使坏大词人张先,看望坡怎样使坏东坡,看8.今之诗人们怎样歌咏这个浪漫故事
9.今天是苏东坡诞辰日,友人相邀小聚纪念,因事不能前往,故作此诗
10.东坡节花絮5:《苏轼全传》首发式
11.海南贬谪文化研究系列(7)∣李景新∣还从庄简觅高风
望坡闲情欢迎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umianhuaa.com/mmhzz/984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