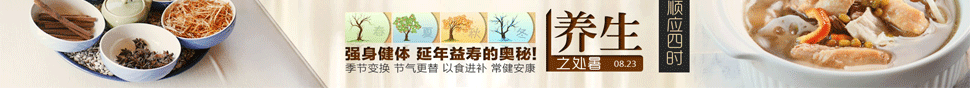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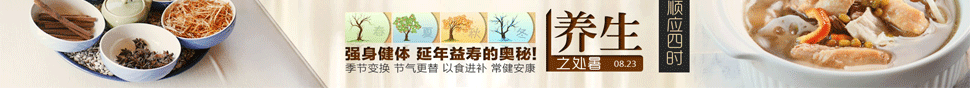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青色
站在高处俯瞰,三坊七巷鳞次栉比的马鞍墙如波涛般起伏,树冠庞大的榕树,站成了一朵朵绿云,栖息在灰瓦上。在如画卷铺开的坊巷,西南角一树红花独秀,高出屋脊甚多。这便是文儒坊大光里8号陈衍故居闻雨楼前的木棉花。
每年三四月份,这株木棉就开满硕大的红花,如百千盏高酒杯擎在枝上,像是在致敬曾经生活在这座院子里的主人。地上离枝的花朵鲜活、红艳,让人怜惜不已。我常徘徊在这拾捡落花,亦在这拾捡巷口飘过的那些许往事。
陈衍,晚清同光体诗泰斗、《福建通志》总纂,室名“石遗”。据说,这是因为他在梦中见所有作品都写满“石遗”二字,故名。大光里(原名三官堂)的这座宅院是他息影归来之庐。木棉花所在的院落位于陈衍故居东侧,额题“闻雨楼”,是陈衍读书、写作、会客的地方,他常在此通宵达旦校勘诗稿。目前仍有其后裔居住。所谓“闻雨”,盖因陈衍喜听雨,在这样的梅雨季节听雨正可引发诗兴吧?院正中这棵高大挺拔的木棉,花开之时,常有白头鹎、太阳鸟、暗绿绣眼鸟在树上鸣唱不绝,像极了当年诗人们在斯楼斯地燕集谈笑、歌诗吟声的景象。若恰逢雨天,同样喜雨的你或许会慢下脚步,细聆雨打芭蕉或雨落木棉蜡质花瓣的声音。雨声淅淅沥沥,阵阵拨动心弦。偶尔,细密的雨裹挟着木棉花跌落枝头,似一声声重重的叹息。
这座私宅布局全由陈衍自己设计,不算大,加上主座(现辟为中华福馆)也不过多平方米。在豪宅林立的大光里可谓陋室,但却以风雅韵致著称,不少文人骚客常在此雅集吟诗,使之成为闽都首屈一指的“诗楼”。这也是我时常探访,找寻诗心的秘境。当年座上宾,如今都成土,但他们遗留的句句诗词不朽。宅院之北为匹园,是陈衍纪念先室、晚清才女萧道管而筑,建筑形如“匹”字。楼上的藏书楼名为“花光阁”,也是因萧夫人之诗句“挹彼花光,熏我暮色”而作名的。
当然,我频频探访这座院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曾经的“诗楼”遍植奇花异草,包括西府海棠、海棠、梧桐、腊梅等。这些花木至今在福州亦不多见,我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可惜,这些陈衍当年珍爱的花木已无迹可寻了。“室人尝言愿筑楼数楹,竹梧立后,花树仰前。”于是,这位痴情的福州男儿便院前屋后种竹植桐,在隙地遍植花木,“斯楼成,先室人已亡十有一年。余为匹夫久矣。匹夫卧楼上,匹妇长卧地下,所谓鳏寡而无告者也,不以‘匹’名吾园,而何名邪?”你爱花木,我便花木绕屋;你走了,世间惟余肝肠寸断一“匹夫”。陈衍的《匹园记》,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萧道管,字君佩,室名“戴花平安室”,自幼饱览诗书,擅诗文,工小楷,与陈衍情笃意深、琴瑟和鸣。如她夫君,萧道管的一生亦著作颇丰,其中《戴花平安室词》只有五首词,首首都与陈衍相关,三首为陈衍代赋。《戴花平安室杂记》中详载二人起居游旅,饱溢夫妻缱绻之情。两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三十载。婚后,陈衍生活困顿,萧夫人时常变卖嫁妆,尝一次典尽七条裙子供其食旅。此等举动,绝非一般女子能为之,令人感佩。
两人志趣相投,常彻夜长谈,以诗文联句唱和。萧道管爱花,在秋天买菊种菊,剪菊瓶供,云:“窗纱厌白地,位以瓶花影。”陈衍便应和,题楹联:“翠袖影婵娟,日暮天寒倚修竹;疏帘风料峭,秋深人瘦比黄花。”夫妇寓居上海西门街时,家中木芙蓉绽百十朵,二人均记下这盛况。萧道管《戴花平安杂记》与陈衍《石遗室诗话》中关于木芙蓉的记录所用字句如同一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吾以中岁奔走四方,无往不与先室人偕一生相偕”,以至于很多年以后,陈衍仍如此慨叹。世间最好的感情,莫过于生活上的伴侣,灵魂上的知音,即使再庸常的日子也会过得活色生香。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站在“闻雨楼”前的木棉树下,我忽然想起了诗人舒婷的这首诗。
本文.5.2刊发于福州日报闽江潮版。感谢编辑老师的抬爱!往期回顾:古厝花木深人间有味是青梅写给春天的第八封情书一溪落花向东流—END—欢迎扫一扫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umianhuaa.com/mmhzz/96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