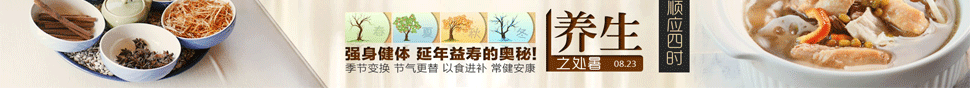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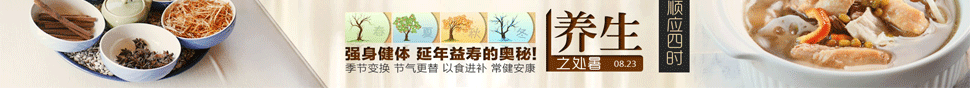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用文字与影像记录生活妄言世事
今晚的这篇文章,作者是我在大学里很敬佩的一位老师。我于网上偶然搜获这篇文章,着实喜欢,便通过微博联系到他拿到了文章转载的授权,在此分享给你们。
很多人总会习惯沉溺于舒适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缺乏改变现状的勇气,畏惧于离开“温泉”,做那只“羊群”之外的羊。或许看完这篇文章,你会有对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更多思考和感悟。
“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
作者:郝朝帅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街边远远近近的木棉花都浓烈绽放了。虽说是四季花开的广州,也只有这样的盛春时节才能看到这些火炬般高擎的红硕花朵。走在路上,不期然间抬头一望,也许就发现头顶上已然连成一片的金红色火海,绚烂得荡人心魄。
就像木棉花对这座城市空间的填满,这座城市的喧嚣也不离不弃地填满我的空间。每天,无论我在书桌前忙活着什么,都会伴随着窗外广州大道上往来呼啸的车流声,昼夜不息。这声音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与喜欢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缺点同理,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喧嚣,因为我更倾心于此刻在广州的生活。
不过我似乎并没有资格如此表态,因为我和我的几位同学不一样,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既得利益者”——早早来这座城市打拼,早早在房价高企之前安居乐业,早早挣下了生存和发展资本,正幸福地享受着大都市的各种好处。我是年近不惑时才举家南迁的后来者,落户不满3年的新移民。年龄既大,白手起家,也无什么“前期积累”。一套面积不大的二手房,就欠下了满山满谷的外债,再加上20年的银行贷款,大几千元的月供……听上去毫无理由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日子,根本让人看不到曙光在哪里。
然而,就是这远离亲朋公里之外的异地他乡,就是这种貌似压力山大的生活,我感到了一种妥妥的心安,感到了一种舒展和轻松。这些,都不是那个我和家人生活多年的北方城市曾经给予过我的。这种体会或许也和今天很多寻梦北上广的人多有不同吧。对于有些人,北上广可能只是他的战场,是他付出斑斑血泪要征服的敌人,只有故乡才是灵魂的栖居地。
我这么说,并非由于在过去的生活中我是一个“边缘人”或“失败者”。正相反,我曾经的生活,在当地算是教科书般标准的“主流”样板。我是在安徽西北部的一个地级市长大(我不用“故乡”来称呼它,是因为直到我11岁时我家才迁居到那里),这个城市人口密集,交通发达,本来基础也不算太差,这些年更是越来越有现代化城市的模样了。不过作为一个根基深厚的农业城市,那里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乡土传统,基本秉行着“熟人社会”的行事风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除去外出读书那几年,我一直没离开那个地方。我所有的生活也都是按照当地常规套路进行:高中毕业出去上大学,再返回本地工作,接着恋爱成家,有父母准备好的一套大房子,生了孩子后老人们再来帮助照看……一切都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在那样一个熟人社会,上下两代人的社会关系积累,也足以对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啰嗦烦心事儿。这种生活,既没有多少压力,也无须去改变什么,“稳稳的幸福”,对,很多人是这么总结的,这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小确幸”。不是也有歌为证么,“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
可是,在很久一段时间里,这种安逸的状态总让我心里不太踏实,总觉着自己的生活有些似是而非。作为比较晚熟的人,我在渐渐弄清了自己是什么人之后才明白:原来,让我活得惴惴不安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都不是我适合的,不是我想要的。比如,我更喜欢在社会中什么事都按“规矩”而不是“人情”来处理,哪怕没有那么多朋友;我更希望自己的个人空间足够独立,而不是被缠绕进各种人际关系和人际事务,为此搭上大量时间和精力;相对于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群,凡事尽在掌握的游刃有余,我更愿意让生活经常出现未知和变数,即便有可能左支右绌;相对于一潭死水般的日复一日,我更乐意接受在一定压力下的生活,这样更能刷出自己的存在感——所有这些,用两个新的英文名词可以大致概括:我在本质上是一名highmover(高度迁移倾向者),却一直作为一名lowmover(低度迁移倾向者)而活着。
我最终决定要从这种生活中出走,纵然已经不再年轻。我清楚地记着,心里是怎样一点一点生长出逃离的冲动,怎样如野草般蓬勃伸展,越来越无法遏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某个冷飕飕的秋天或冬天的下午,站在家里的大阳台上,看着下面略显萧瑟的马路和晦暗的天空,心里就弥散开大片大片的荒凉。我的一生真的就要这样没精打采过去吗?就要在这个无比熟悉的小地方终老余生吗?在这个平滑的循环轨道上,未来的日子还没开启就已经看到了全部,想想都觉着绝望。我要离开,一定要离开。纵然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全部少年和青年时光,纵然这里还生活着我的母亲和其他亲友,但我已经对它无所依恋,这里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进入一线城市北上广吗?这些地方能满足我对理想生活的全部想象吗?或许是的,我正是选择了北京度过自己的最后4年求学生涯,然后再度择业选择了广州。人们通常认为,是机会、财富、优质的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吸引人们来到北上广,但这绝不是全部。在这些具体的物质性要素之外,在北上广整体的城市气质中,还是有着可归结为精神或情怀的东西在召唤着人们。作家徐则臣在去年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说,“到世界去。”世界,意味着常识以外的生活,意味着更多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可能。而北上广就是普通国人目力所及之处最具备“世界感”的地方。就像北京,“不宜人居,但它宽阔、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至于广州,则是更加包容、平和、亲民,生活在其中能够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尊严和尊重。我们说,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群体归属感,以及在这些基础之上形成的整体安全感,都是人生的必需品。如果你很幸运,在家乡就得到了这些,那么恭喜你,你不用到世界去了。如果在家乡得不到这些而又不愿意委屈自己,你势必就要走进“外面的世界”来寻找。如果北上广仍然无法妥帖安置自己的心灵,那么就要继续找下去,直到找到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男主角初平阳就是这样。
3年前当我去意已决的时候,身边有的亲友非常不赞同:折腾啥呢,快40的人了,活得好好的,怎么就容不下你了?面对这样的声音,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形而上”层面,这背后支撑的就是各自的“人生观”或者说“幸福观”,人和人之间是这样的不同,根本无从辩论出谁是谁非。你没有理由反诘我的任性出走,我也没有资格嘲笑你的保守狭隘。或许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出去得太晚了点,闯荡世界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我人近中年了却还要执着地带着一个家庭离开,当然显得不合时宜。只是我相信,只要愿意行动,任何时候都不算晚,不是吗?
3年后的此刻,窗外车流声呼啸如常,在温暖潮湿的空气中,浓郁的春天正汁液饱满地伸展。这里长夏无冬、春秋相连的气候,让北方的老母亲很是喜欢。皖西北的冬季很冷,当地又没有公共供暖设施,最近3年中的两个冬季,她老人家都是飞来广州度过的。在户外穿着薄毛衣过冬的经验,老人家还是从未有过。而且,每次往返广州,母亲都是逆着春运的人潮走,来回都能享受超低价位的折扣机票,这一点老人家很满意。现在,她显然已经喜欢上这种“候鸟”式的生活,今年离开的时候,把一批衣物都留下来了,以便来年的冬季旅行更加轻装上阵。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音乐/生如夏花-朴树
图片/后会无期剧照
编辑/二蚝
作为一名广州人,很开心看到郝老师能在广州觅得一处可心安的寄居之地。但常年身处南方的我,倒是很想找机会去北方看几眼。
下学期的公选课名单里没有他的课,颇为遗憾。那我就努力去蹭中文系的课吧哈哈哈。
有缘再会:)晚安。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
钙泊三醇软膏钙泊三醇软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