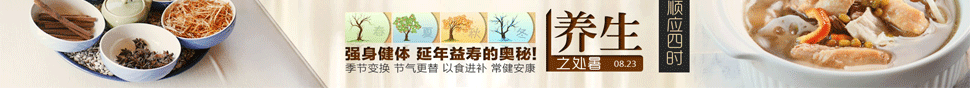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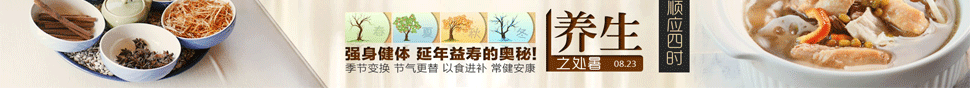
枝叶葱茏,
宛若闺秀。
下过一场暴雨,福新路路口,新华都边上的那棵鸡蛋花树,亭亭如盖,神采奕奕。
相对于它的花,我似乎更喜欢它的叶子。
鸡蛋花树碧绿的叶子,叶形有点像枇杷叶,但叶上没有茸毛,叶脉在近叶缘处连成一边脉,像一条鱼的鱼骨似的,比枇杷叶更来得清晰一些。
也有点像杜英叶,但比杜英叶更大、更有厚实的质感。
鸡蛋花是夹竹桃科灌木、或落叶小乔木。别名缅栀子、蛋黄花、印度素馨、大季花等。
它的花边缘乳白色,瓣心金黄色,犹如摊开的煎蛋。这应该就是鸡蛋花得名的由来了。
我在福州,却没有见过比福新路这棵更大的鸡蛋花树了。
人立树下,幽香扑鼻,比白兰花与桂花,更有一种闺秀之气。风过处,偶有一两朵花朵落地——
鸡蛋花的花,聚生于枝顶,每一朵花都由五片花瓣轮叠而生,如同孩子们手折的纸风车。花瓣肥厚如木棉,落花也宛若木棉,吧嗒一声,落地后,依然是完整的一朵。
虽然不似其他花种的落花那么缤纷,却给人一种难得的闲静感。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以本地生长的植物入馔,广东人更是。他们连口感一般的隔壁邻居福建人都吃,如此丝绒般丰腴、肥腻的鸡蛋花,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广东人常用木棉花煲汤、入药、泡茶。
也常用白色的鸡蛋花(注意:白色的可食,红色的有毒)做凉茶、煲汤。二者都能清热、利湿、解暑、排毒。实际上,岭南一带茶铺里的五花茶,就是以鸡蛋花、木棉花、金银花、菊花、葛花为主料熬制的。
两个不同的树种,却有着太多的冥冥暗合。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是这么描述鸡蛋花的:
“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则黄,有香甚缛,落地数日,朵朵鲜芬不败。”
六瓣,肯定不会是六瓣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是六瓣的。
不知是观察上的疏忽(屈大均号称广东徐霞客,不可能将五瓣看成六瓣。况且,他连鸡蛋花“瓣皆左纽”的微小细节都能注意到),还是传抄刻印手民误植,反正在《广东新语》里,鸡蛋花就成六瓣。
鸡蛋花的生命力很强。
从树下折来一根树枝,插入泥土里,生根发芽就是一株新苗。无需费心打理,有水有阳光就蓬蓬勃勃,独自美丽着它的美丽。
在我国西双版纳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人们普遍信奉南传佛教。根据佛教教规,除必有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不少于5个僧侣外,寺院里必须种植的“五树六花”。
五树,指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
六花,是指荷花(莲花)、文殊兰、黄姜花、鸡蛋花、缅桂花(白兰花)和地涌金莲。作为六花之一,鸡蛋花在这些南传佛教盛行的地区,被广泛栽植,又称“庙树”或“塔树”。
如果说,琴叶珊瑚的树形像珊瑚,那么,鸡蛋花的树形,就是大了几号的珊瑚。
它的树干虬曲多变,枝条粗壮,枝干常为三叉分枝,秋冬叶子落光后,剩下的树枝,看起来也像鹿角,故又称为“鹿角树”,观赏起来也别有一番趣味。
鸡蛋花常被用作南方城市的景观树。尤其在岭南一带。
在广东一些地方的老式庭院、祠堂天井里,常常见到鸡蛋花。南方人的家常精致,离不开四季花木,鸡蛋花和桂花、石榴、海棠一样,是拥有庭院气质的闺秀型花木,适宜守家护院。
鸡蛋花生得葱茏丰腴,花香流溢,有着淡淡的古典画意。
我喜欢向晚时看花。如果有夕照的话,更好。夕照里的鸡蛋花,像旧电影里的画面,格外温润柔软,看映花晚照,有如旧日的时光,渐渐隐没在万家灯火的暮色里。
我喜欢鸡蛋花,也许最喜欢的,还是它落落大方的姿态吧。
它端庄素雅,不卑不亢地生长着,生活着,在有序的四时里灿然风华,自成一格。
正如《如花在野》田中昭光所言:“花应四季开放,花开人心自安”。还有什么样的璀璨艳丽,能比人心自安这四字,更来得满足,来得安恬呢?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umianhuaa.com/mmhsj/9663.html


